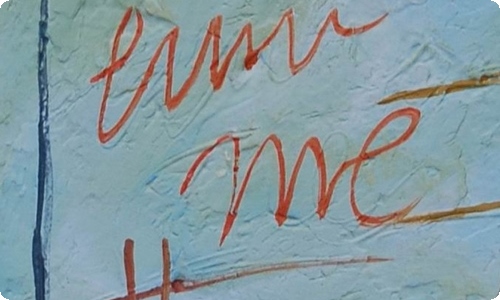林清玄的经典散文【多篇】

[概述]林清玄的经典散文【多篇】为网友投稿推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 篇一然而好的散文却绝不是散乱无章文字之堆砌,前人所谓“形散而神聚”是对散文较为客观公正的界定。刘勰说“结体散文(行文),附物切情”更是可做散文最好的注脚。或如海,或碎小如芥,都会凝结于一个核心,蕴结出一种情味。七情动而五味起,精气凝而文章生。所有的散文都是这种精气神的聚合体,将作家情感之激变,思想之机巧,熔于一炉,炼成一篇荡气回肠、回味无穷的大手笔,击响万代,芳流千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应该属于当代最具这种精气神的神圣之作。贾平凹的《丑石》是上乘美文,毋庸置疑;林清玄的《心田上的百合花开》是禅味的奇葩,亦无可厚非;刘成章的那篇《安塞腰鼓》笔意锐利,气势雄浑,也堪称壮阔手笔;而《我与地坛》则将贾平凹的淳朴灵动,林清玄的哲理禅思,刘成章的壮阔大气尽皆吸收,史铁生在他残损的躯壳内锤炼锻造,用自己对生命的睿智思考,写就了这样一篇殊为另类的长篇散文,不见斧斫,浑然天成。
可以说,这部作品之所以荡气回肠,关键在于其文字里行间的那种凌越于个体本身之上的彻悟与超然。我们总是对得道者尊崇备至,得道者的至高境界则在于他能拥有一颗平常心。面对万事万物的纷扰嬗变,泰然恬静,是说到容易做到难的。所以我们总是远观得道者敬之,近接得道者则常常鄙之的缘故。道不高深,难在付诸行动。世上的人,以宣教扬名者居多,以力行流芳者鲜有。究其根本,在于达不到境界。所以我们说追求浮名者,利禄纠结其心,永远不能成圣;而淡然处世者,心行更远,苦茶野菜裹腹,冶心炼性,关注众生而终成大我。轮椅上的这个生命,如是。
一座封建帝王顶礼膜拜的地坛,沦落为一座被高楼大厦湮没的荒园。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之下,它无辜的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病后第一次进入地坛的史铁生,就在带着疾病对灵肉双重的折磨中,悲壮地进入了这个园子,那种感觉,就像是翘首以待的老妇等待沙场归来的儿子。史铁生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儿子。地坛本身的命运因历史的沧桑而厚重沉郁,荒草颓墙虫鸣鸟叫在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在无形左右着一个人脆弱的灵魂。直到那个一直闪躲于丛草树荫的老妇,用她的爱与坚韧燃尽了生命之火,史铁生才觉得,自己也是那个妇人的儿子,也承继了她大部分的品质。一座古园历史的变迁与一个生命悲喜的反差推动了这个生命主体的升华。就在这座游离于都市罅隙里的地坛,史铁生用他的静默独思完成了灵魂的救赎与精神的涅槃。
史铁生没有停步于个人的世界,他透过文字告诉我们,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与历史之间,生命与古迹之间,是有联系的。而这是他通过自己的灵魂窥察地坛所内蕴的命运本真所获得的。他让这种生命的顿悟,在细腻缠绵的文字流淌中,沁入每个读者的心灵。所以说,《我与地坛》并不是一篇简单意义上的散文。你走进文字,就会在一个自己生命中也有其影迹的荒园里,捕捉到自己心灵的脉动,聆听到造物的声音。
真正超越时代的鸿篇巨著就是让读者在这样漫漫扬扬的文字挥洒中不觉其繁琐,在平淡无奇中不觉其乏味。掩卷闭目,内心必有所得。史铁生的生命与灵魂,融于这座曾经的荒园中,也凝于这篇必将流传下去的经典散文中了。
作为一篇经典散文,《我与地坛》已成一部文学的神话。解读这篇散文,我们就能够洞悉经典散文具有的特质。
即使是这个散文作品遍地开花的时代,能够称得上经典的散文依然屈指可数。大部分的作品要么局限于抒发个人的不平之鸣,要么思想局限于利益层面,带有鲜明造作的意识形态标签。而经典的散文则能突破这些局限,能用千锤百炼的语言来沉稳从容地走入人心,直面灵魂,剥开禁锢思想的硬壳,解放思维的翅膀。由诗性的语言传递理性的光芒,冲击每个读者的灵魂。
卓越的散文是一种超越文体而存在的精神呈现方式,立足于作家本体的生命体验,注重于精神思想的解剖,着眼于对生命群体的思考。惟其有内在如此之深邃,才有其文辞意蕴之隽永。不媚俗不标榜,不追求文化消费的功利,固守散文保有理想弘扬精神呵护心灵的本色,能在不显山不露水之间,取得给读者的生命导航、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的效果,这就是经典散文超越历史的思想价值之所有来。
阅读这样的散文,读者才会在文字的漫溯中,领悟到作者的精神寄托,接受其思想的熏陶,开启自己的心扉,升华自己的灵魂。而这样的散文也才在读者的认可与咀嚼中得到生命的永恒。读者与作者,在散文文本所织构的思想家园里共鸣了,也永生了。这也就是史铁生所说的“众生度化了佛祖”。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 篇二关键词:林清玄;童年时代;菩提智慧;生命体验;禅理散文
关于林清玄
林清玄,台湾高雄人。当代著名散文家之一,连续十年雄踞“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榜单”。被誉为“天才作家”。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主编、主笔等。
八岁立志成为作家,十七岁正式发表作品;二十岁出版他生平的第一本书《莲花开落》;三十岁之前得遍台湾所有文学大奖;三十二岁遇见佛法,入山修行;三十五岁出山,四处参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最畅销的作品;四十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被推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之一,同时创作的“现代佛典系列”,掀起学佛热潮;五十岁完成《茶言观色》《茶味禅心》和“人生寓言系列”,被选为青少年最佳读本;五十二岁完成写作奥秘三部曲《林泉》《清欢》《玄想》,被选为中学生优秀读物。
林清玄的文章曾多次入选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中小学国华语材及大学国文选,他的《光之四书》(《光之香》)一节曾被收入大陆高考语文试卷,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其作品风靡整个华人世界,被海内外誉为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华语散文作家之一。
林清玄的童年时代
一、对林清玄的潜移默化
童年时代的林清玄生活在一个有十几个孩子的农民家庭里,但这个大家庭却是一个气氛极为浓厚的家庭。父亲以上三代,对寺庙事物都非常热衷。为了回答先辈们的这种举动,如云: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如此为宗教活动忘情忘身地参与?我想有两点,一来是基于崇敬祖先的心理,因为寺庙所供奉的神明,大部分是我们的民族伟人。二来是那些层出不穷的神奇现象,确实带给了民众强烈的鼓舞力量。①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不得不让林清玄学着去感知、体味宗教。林清玄说:从小,我便经常随着父亲四处区参拜。 正是这种宗教思想的潜移默化使得林清玄从小就对有着强烈的崇敬。然而,在这些言之凿凿的神迹及浓烈的宗教气氛之外,我也开始有了些反思。[1]
二、林清玄与同龄孩童的现实世界
童年时代的林清玄有吃母亲烧的红心番薯的欣喜,有看父亲放鸽的乐趣。可以为了得到一块糖果而和母亲弄别扭,可以为了一直丧生的小松鼠而抱头痛哭。它的童年在物质上虽然是贫穷的,但他在精神心灵上是富足的。 如云:“生活品质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因而有自 ……此处隐藏13521个字……,后又毕业于中央陆军官校;还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他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也曾与后来是“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一同起居办报”。
1964年获美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又做过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和哈佛大学研究员。《剑桥中国史》的研究班子里也有黄先生的身影。
试想,一个人有如此复杂丰富的经历,又经常在政治、经济、历史、学术等领域与一拨拨 “高人”相处,加之独特的思维方式,不出一点思想成果,可能吗?
又读黄仁宇,觉得历史大可亲近;而现实的浮躁实在该要冷却一点了。
三、读林清玄
连续读了陈寅恪、吴宓、辜鸿铭、胡河清等人的著作或传记以后,感到十分的累,于是翻出早些年买的《林清玄散文》。
这感觉好像电视台采访“东方之子”,访了好几位学者老人,然后访一两个年轻俊彦,以作调适。
“林清玄”似清茶,淡淡之中有可品味的东西。
林清玄是1953年生人。30岁以前,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想做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想写出“名篇”,想升官,想发财。后来,其父去世,他于是顿悟:时间就是生命。“也许你可以一个早晨赚1000万,但1000万却买不到一个早晨。”于是他从此贯彻“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这一刻”。
曾见不少少男少女膜拜港台影星歌星,那自然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嗜好,一如喜吃地摊夜宵,快活嘴巴是肯定的,营养卫生就难说了。倒不如“走进”林清玄,一如风味别致而又不乏营养的餐馆,更划得来。
林清玄说他自己的写作有“三部曲”:开始,毕业后到报社做记者,写文章求的是要人感动,要人叫好;中间,把文章当表达的工具,真实地写出自认为值得一写的东西,没有风格;后来,撰写佛学题材,写作目的是希望读者能有所感受。
一位学生告诉我,“有一天情绪很坏,顺手翻到了同学床上的《温一壶月光下酒》,就看下去,结果把书看完了,那一个星期心情都清清淡淡,爽爽的。”
我想林清玄散文是有这样的“法力”的。尤其对年轻人士。他的《菩提系列》十余本书更是启人心智,开悟愚顽。
林清玄说:“一次“在松树下午睡,我被松后寺庙的钟声唤起。我坐起来,仿佛那些声音都是从我的左手流进,右手流出,在体内川流不息,我觉得自己是大地的一部分,松树也是,连庙里的钟声都是。”
读林清玄,是把鄙俗的生活抛到了九霄云外,然后着一身松弛的棉布衫,心盈盈乘着海水,融解着平凡的生活。
林清玄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和不疲倦的佛学宣讲者。他在创作成熟期,平均每月出一本书。当然不能说他的书本本皆精品,但至少精品在他的作品里是主流。
关于林清玄的传说甚多。什么“有人见到他以后下跪祈福”;什么“少女痴迷于他”;什么用他的书当“法药”,不一而足。他自己却说:“其实我很平凡,就像我至今还是有点不满意,为什么我太太总不拿我当作家看,老是叫我洗碗一样。”
我素来以为,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有三种境界:一境为真实、取坦然;二境为独执己见,不合流俗;三境为忘我、超然。三境居其一就可爱,居其二可敬,三者皆备则可奉为永远的师友。
不敢断言林清玄三境皆备,但至少一境二境可达,所以读其文是不会有上当之感的。现如今,书海无涯,假劣伪书喧嚣热闹,益发显出林清玄的好处来。
那就来吧,在清幽的林中去找寻一份“玄意”。
四、读龙应台
见到不少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的“见闻录”或是“纪实”之类的作品,挑一些读过,不太喜欢那种炫耀中夹杂顾影自怜夸大其辞以及个人臆测式的文字。读了龙应台的《人在欧洲》,味道迥然不同。我不排除对龙应台先入为主的好感,但书中的所言所评,的确言之有物,评之有理,思之有深意。当然不是走马观花卖弄一点皮毛的“二道贩子”把戏。
这有个先决条件。l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的龙应台,23岁即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在纽约的两所大学先后任教多年。l986年,她旅居瑞士苏黎士。两年后又迁居德国法兰克福。
以一个作家的实地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学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做“底子”,来述说“人在欧洲”,那种文蕴文味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龙应台非“蛇应台”。“龙旋风”l985年在台湾报界、文坛以《野火集》威震宝岛,1988年这股旋风又席卷大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系列文章令两岸中国人为之一震。
与柏杨的嬉笑怒骂、李敖白眼冷视不同,龙应台把男性的犀利与女性的细腻结合到了一起,在冷峻的批评之中可以触摸到滚烫的心。
某年深秋,龙应台曾来湖南。弘征先生撰文写到这一回事。弘征先生未见龙应台之前,想象这个刮起冲天“野火”的女性“是一副睥睨天下的‘女强人’派头?还是冷若冰霜,俨然一尊大学者的模样?”一见面,却见她“一套浅色西装套裙,散淡、随意、和谐”,无一花哨饰物,“说话如细雨飘飘”,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在凤凰的街巷看到几个孩子吹泡泡糖,急忙去寻一个小摊买了一版,炫耀她在台湾5岁就吹过,嘲笑弘征刚才回答那是吹肥皂泡泡。在去湘西的途中,车在半路抛锚,正好来了一辆在乡村既载人也载货的小型农用车,她坚持坐这辆车启程,并且跟农人们有说有笑。正如她自己在《龙应台这个人》中所招认的:“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
无论读《野火集》还是《人在欧洲》,“恨恨”的文字外壳里面,细一触摸,却是博爱的内核。只是这种爱埋得很深罢了。
龙应台写到,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见一对黑人夫妇牵着个小女孩,黑孩子一手紧搂着洋娃娃,也是个黑娃娃。这次她吃了一惊。由此说开去,她有了新见解:“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级之间。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又是另一番心态。”
在12万字的《人在欧洲》中,客观地分析,冷峻地批判,鲜活地见解俯拾皆是。与《野火集》稍不同的是,你也可以把这一本书当“消闲书”来读,看欧洲人的心态,看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与“定位”。
我时常读到一些中国人在欧洲在外国如何获奖,如何受欢迎,如何获得“雷鸣般掌声”等等文字,我也相信其中不乏事实;但是,据龙应台旅欧多年所见所闻,这样的“美景”不说没有,至少是很少。因为一些国人的“吹嘘”全然忘了西方世界的基本心态。比如龙应台所写的洛伽诺国际笔会,90篇论文,亚洲人只有两人被安排上台去念。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还被安排到最后,无人耐烦听的时候去发言。这与我平素听到的“新闻”似乎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说,《人在欧洲》又给了内地读者不少真实的信息。
一本书,给人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给人许多深刻的见解;给人许多智慧的光亮;这本书值得一读。我甚至想绝对化:龙应台的作品全在可读之列。一个作家的人品、文品,决定了其人存在价值。
你也可以在搜索更多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其他林清玄的经典散文【多篇】范文。

文档为doc格式
- 【精品】教师实习总结模板集锦七篇[本文共13000字]
- 2022年综合办公室工作计划[本文共2143字]
- 行政前台个人年度工作总结(多篇)[本文共17057字]
- 生活困难补助申请书精品多篇[本文共4898字]
- 初中教师校本培训心得体会多篇[本文共8271字]
- 居间合同书(精选15篇)[本文共21860字]
- 工作队进驻某村脱贫攻坚工作总结[本文共2512字]
- 小学体育教师年度考核个人工作总结多篇[本文共6329字]
- 服装管理的制度多篇[本文共5173字]
- 高中政治老师教学反思[本文共4424字]
- 大学贫困生助学金申请书精品多篇[本文共3077字]
- 写给老师的一封感谢信作文精品多篇[本文共2708字]
- 居间的合同【推荐】[本文共26808字]
- 学生写给老师的颁奖词100字(精品多篇)[本文共1121字]
- 赤壁赋原文翻译(新版多篇)[本文共6075字]
- 晚会活动领导简单致辞[本文共3719字]